建筑的表征

当你走进故宫太和殿,抬头仰望那些雕刻着蟠龙的立柱时,是否想过它们不仅仅是支撑建筑的结构构件?这些立柱不仅承载着屋顶的重量,还传递着帝王权威、天地神灵的象征意义。同样地,当你站在天坛祈年殿前,被那完美的圆形对称与蓝色琉璃瓦所震撼时,你是否意识到,这种独特的空间布局和形制,并不仅仅是工程师的巧思,而是在展现天地宇宙与秩序之间的神秘关联?建筑真的只是为人类活动提供遮蔽和便利的工具吗?还是说,建筑在每一根梁柱、每一道门窗、每一个空间的布局中,都在传达某种超越物质功能的信息?它是否同时在塑造人们的共同记忆,参与文化身份的建构?
关于“建筑是什么”这个问题,答案远比表面上更为复杂丰富。建筑确实首先具有满足实用需求的功能,比如提供遮风避雨、组织空间流线、保障安全等。然而,若只将建筑视为纯粹的工程产品,我们便忽略了其作为“表征”的另一重身份。所谓表征,指的是事物以可感知形式承载、传递、表现复杂观念和情感的能力。正如一幅肖像画,不只是再现人物的外貌,还蕴含画中人的性格、情感和所处时代的印记;同样,建筑通过比例、色彩、装饰、材料、空间序列等要素,表征了超越其物理形态的价值体系、审美追求、宗教信仰以及社会权力结构。
要深入理解这一点,我们可以从中国的传统建筑与现代建筑两个对照鲜明的领域入手。中国传统建筑中,诸如宫殿、寺庙、祠堂,每一项细节都承载着特定的礼仪、伦理与宇宙观。例如,太和殿九脊十八兽的屋顶象征着皇权无上,殿前广场的层层台阶与中轴线强调肃穆和秩序。这些设计并非偶然,更是一种文化编码。到了现代社会,建筑师们在高楼大厦、地标建筑、文化中心中,依然试图用新材料、新技术构筑意义的空间,反映现代性的理想与张力。比如北京国家大剧院,用巨大的椭球体和水镜面投射艺术的纯粹与当代中国的开放姿态。
虽然这些建筑距离我们的日常生活似乎很遥远,但正因为这种距离,我们更容易冷静审视、敏感捕捉它们在表征层面的深刻意义。建筑既是历史的见证者,也是社会变迁、文化传承与集体心理的物化表现。回望人与建筑的关系,其实是不断追问“我们是谁”“我们希望成为什么样的共同体”的过程。正如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所说:“空间本身就是社会关系的产物。”建筑的表征性,正是这种空间社会性的最好注脚。
装饰与结构的融合
故宫太和殿的龙柱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例子。这些立柱表面雕刻着精美的盘龙图案,龙身蜿蜒盘旋,鳞片清晰可见,栩栩如生。这些雕刻显然是表征性的艺术作品,它们描绘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皇权的神兽。但这里产生了一个有趣的问题:这些雕刻是建筑的一部分,还是仅仅是附加在建筑表面的装饰?
如果我们认为这些雕刻只是表面装饰,那么它们似乎与建筑本身无关,只是为了美观而添加的元素。但实际情况远比这复杂。太和殿作为皇帝举行大典的场所,其真正的功能或许并不是简单的遮风挡雨,而是营造一种庄严神圣的氛围,彰显皇权的至高无上。从这个角度看,那些龙纹雕刻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,而是建筑核心功能的体现。
再看现代建筑的例子。国家大剧院的整体造型是一个巨大的椭球体,表面由钛金属和玻璃构成,在水面的倒影中呈现出完美的对称。这种造型本身就是一种表征——它象征着艺术的纯粹性、音乐的和谐性。结构与表征在这里完全融为一体,难以分割。
上图展示了传统建筑与现代建筑在不同特征维度上的侧重点。传统建筑在装饰元素上的投入较高,而现代建筑更强调象征意义的直接表达。但无论哪种类型,建筑都不可避免地承载着表征功能。
中国古代建筑中还有一个普遍现象值得注意。许多木构建筑的石质版本保留了原木结构的形式特征。比如斗拱这种构件,最初是木构建筑中解决受力问题的结构设计,但后来在石质建筑中仍然保留了斗拱的形态,尽管石材的力学特性完全不同。这意味着什么?这意味着这些石建筑实际上是在“表征”更早期的木建筑,它们用石头“再现”了木头的建造逻辑。
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个别建筑中,而是贯穿整个建筑历史。建筑师往往会模仿、引用、改造前人的设计,形成一条漫长的表征链条——每一个设计都是对前一个设计的诠释和再创造。走在中国任何一座历史城市的街道上,你都能看到现代建筑借用传统建筑的檐口、斗拱、窗棂等元素,这些引用构成了建筑文化的传承脉络。
柱子与人的身体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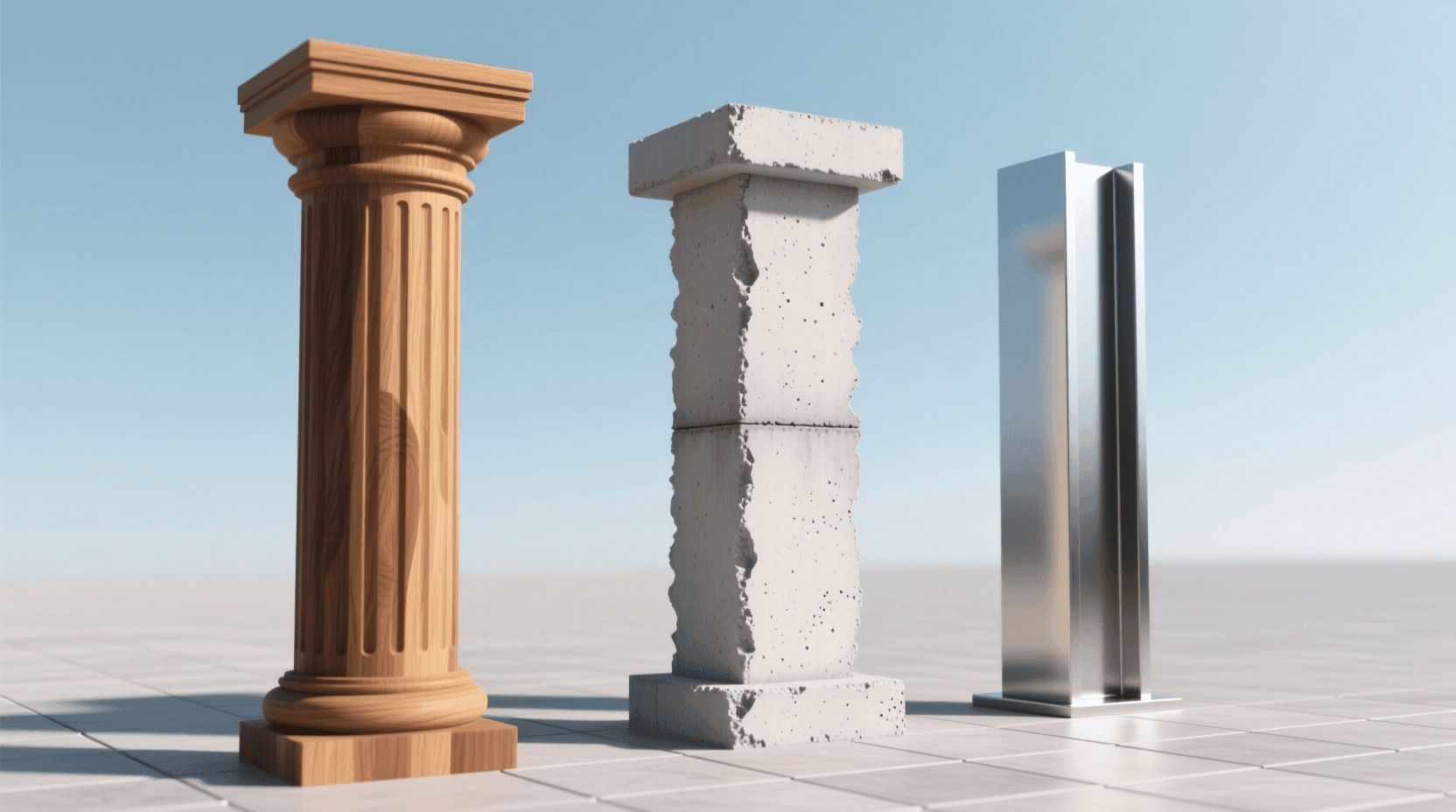
在故宫的某些殿宇中,柱子不仅仅是柱子。它们有的雕刻成龙的形态,有的涂绘着精美的图案,有的则保持着木材的原始纹理。但无论外表如何变化,所有的柱子都在执行同一个基本功能:承载重量。
人体也在承载重量。当一个人站立时,腿部肌肉和骨骼承受着整个身体的重量;当一个人扛起重物时,脊柱成为主要的承重结构。这种承载的体验是如此普遍,以至于我们在看到建筑中的柱子时,会不自觉地将其与站立的人体联系起来。这不是理性分析的结果,而是一种直觉的共鸣——我们似乎能感受到柱子承受的压力,仿佛那压力作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体上。
建筑柱子与人体站立姿态之间的关联,揭示了建筑表征的一个重要层面:建筑通过形式的相似性,唤起人类对自身身体经验的共鸣。
这种联系背后隐藏着更深刻的真理。一根柱子要站立,必须有地面支撑;地面之所以能提供支撑,是因为地球的引力。同样,人要站立也需要地面和重力。地面与天空构成了我们生存的基本框架,它们不仅是我们观察到的外在现象,更是塑造了我们身体形态和运动方式的根本力量。
人类的身体在数百万年的演化中,逐渐适应了地球的重力环境。我们能够直立行走,能够判断水平与垂直,能够在平衡中移动,这一切都源于身体与地球环境的完美契合。当建筑中的柱子垂直矗立时,当建筑的地面保持水平时,这些设计不是偶然的,而是对人类身体特性的回应。
上图展示了木柱、混凝土柱和钢柱在不同直径和高度下的承载极限。可以看到,随着材料强度的提升,同等尺寸下钢柱能够承载的重量远超混凝土柱和木柱,并且允许建造更高更细的结构。然而,不论材料如何变化,所有柱子都依靠垂直受力来支撑上部结构,这一原理和人体站立时下肢骨骼承重如出一辙。
正因为如此,我们将建筑中的柱子与人体的站立状态联系起来,不只是表象上的比拟,而是因为它们都在面对相同的地球引力和物理规律,以各自的方式实现稳定和平衡。
建筑中的规律性
天坛祈年殿是研究建筑规律性的理想案例。这座建筑呈现完美的圆形平面,三层檐顶层层递减,形成向上收分的优美曲线。二十八根柱子均匀分布在圆周上,形成放射状的对称格局。无论从哪个角度观看,建筑都呈现出相同的形态。这种对称性被称为“轴对称”或“旋转对称”。
与之不同,故宫的整体布局体现的是“双侧对称”。以中轴线为界,左右两侧的建筑、庭院、道路几乎完全对称。这种对称性贯穿了整个紫禁城,从午门到神武门,绵延数公里。
建筑为什么倾向于对称和规律?一种常见的解释是实用性:对称的设计便于施工,重复的构件可以批量制作,降低成本。但这个解释在古代建筑面前显得苍白无力。太和殿的每一根柱子都是工匠手工雕刻的,每一块砖瓦都是单独烧制的,要达到高度的一致性和对称性,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。这显然不是为了省事。
古代建筑的对称性和规律性是刻意追求的结果,是建造者献给天地的一种敬意,是秩序战胜混乱的象征。在那个没有机械化生产的时代,规律性本身就是一种奇迹。
人类的身体是双侧对称的。这种对称性不仅体现在外表——左眼对应右眼,左手对应右手——更体现在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中。我们习惯于将世界分成对立的两极:左与右,上与下,内与外,动与静。这种二元思维模式深深植根于我们的身体结构中。
当建筑采用双侧对称的形式时,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类身体的这种基本特征。尽管一座宫殿的外形与人体相去甚远,但它们共享同一种组织原则。建筑的对称性因此成为人类经验的一种表征。
现代建筑有时会刻意打破对称和规律。北京的中国尊(中信大厦)采用了不规则的切角设计,外立面的角度在不同高度上发生变化。这种不规则性是有意为之的设计选择,而这种选择之所以能够产生效果,恰恰是因为规律性是建筑的常态。不规则建筑通过否定常规,来传达某种特殊的意义——也许是创新,也许是挑战,也许是对传统的质疑。
上图展示了不同建筑的对称性程度。传统建筑往往具有极高的对称性,而现代建筑则在对称与不对称之间寻找平衡。但即使是最不规则的现代建筑,也在某种程度上遵循着某种内在的秩序。
建筑的节奏

节奏这个词通常与音乐联系在一起,但它同样适用于建筑。颐和园的长廊是理解建筑节奏的最佳例子。这条长廊全长728米,由273间相连的廊间组成。每一间的宽度相同,柱子的间距相同,梁架的结构相同。当你沿着长廊行走时,这些重复的构件在视野中以恒定的频率闪过,就像音乐中规律的鼓点。
这种重复产生的不是单调,而是韵律。因为在重复的框架中,每一间廊顶都绘制着不同的图案,每一个视角都能看到不同的风景。重复的结构提供了稳定的节奏基础,变化的细节则在这个基础上演奏出旋律。
建筑的节奏不同于音乐的节奏,它不在时间中展开,而是在空间中延伸。但当人在建筑中移动时,空间的节奏就转化为时间的节奏,静止的建筑在观察者的行走中“动”了起来。
外滩的万国建筑博览群提供了另一种节奏的例子。不同年代、不同风格的建筑沿黄浦江一字排开:古典主义的海关大楼,装饰艺术风格的和平饭店,新古典主义的汇丰银行大楼。这些建筑的高度、进深、立面分割各不相同,但它们共同形成了一种复杂的节奏。如果说长廊是简单的“咚咚咚”,那么外滩建筑群就是交响乐中复杂的复调旋律。
建筑立面中的节奏,正是重复元素在空间中的组织方式。比如图表中的均匀节奏,就好像一排尺寸和间距完全相同的窗户或柱子,每个元素彼此等距地排列,带来稳定、有序、统一的感受。而渐变(变化)节奏,则表现为窗户或柱子的大小、间距逐步递增或递减,仿佛引导着视觉向一个方向流动,强调动态、动势和空间的延伸。
这些节奏方式不仅仅是外观装饰,更根源于人类对秩序与变化的需求。例如,连续等距排列的窗户让人联想到整齐划一的步伐,带来理性和平稳的心理感受;而渐变排列则如同行进、奔跑或音乐的旋律,富于生命感和引导性。建筑师常常通过在建筑立面上运用这两种节奏(均匀或渐变),在统一与变化之间寻求平衡,塑造建筑的整体氛围,并唤起人的生理与心理共鸣。
人类的身体是地球环境塑造的产物,而地球的运转也呈现出周期性的节奏。建筑中的规律性和节奏性,因此成为了这双重节奏的表征。当我们置身于一座规律而富有节奏的建筑中时,我们感受到的是与自身身体、与地球环境的和谐共鸣。
表征的多重层次
通过前面的分析,建筑作为表征艺术可以展现出多个层面,这一点已经逐渐清晰。首先,最直观的层面在于建筑物上的装饰性雕刻与绘画,这些具象艺术常常直接描绘诸如龙、凤、花卉等具体形象,承载着丰富的文化象征和社会寓意。其次,建筑在造型、结构或元素的引用和模仿中,也在进行着历史与文化的表征。例如,不同历史时期的风格元素被新建筑继承和转化,形成文化传承的链条,将时代与地域的记忆封存在空间之中。第三个层面,建筑还可以通过类似“形式的隐喻”来表征其它事物,比如柱子和拱券暗示着站立或举起的身体,屋顶曲线让人联想到山脊、潮水,也可能唤起某种情感或联想。更抽象地,建筑通过对称、比例、节奏、重复等形式语言,来表征人类对秩序、均衡、生命律动等经验世界的普遍感受。
这些不同层次的表征不仅独立存在,更是彼此交缠、相互作用。一座建筑往往同时承载着多个表征系统:既有直观、具体的装饰意义,也有历史的回响与文化的线索;不仅唤起人们对现实物象的联想,还为感官和心灵提供抽象的节奏、韵律和氛围体验。这些表征编织出一张丰富而复杂的意义网络,使建筑不再是单一功能或形式的容器,而成为承载并传递多重意义的文化实体。
然而,我们如果仅以列表方式罗列这些表征类型,依然难以把握“表征”这个观念的本质。表征不仅是建筑的一项附加“功能”,也不仅仅是装饰或象征那么简单。实际上,表征是建筑存在与人类产生深度关系的根本机制,是人类通过空间、材料、形态去理解并主动建构世界的基本方式。正因为如此,建筑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它的物理轮廓,它成为了我们组织、认知、感受生活世界的重要媒介。
意义的建构
人类生活在意义之中。当我们睁开眼睛,我们看到的不是杂乱无章的色块和形状,而是桌子、椅子、房间、街道。当我们竖起耳朵,我们听到的不是无意义的声波振动,而是话语、音乐、车声、鸟鸣。这种将原始感官信息转化为有意义事物的能力,是人类智能的核心。
这个能力如此自然,以至于我们很少意识到它的存在。但偶尔,某些特殊情况会让这种能力的存在显现出来。比如当我们盯着一个汉字看得太久,突然会觉得这个字变得陌生,不再能够识别它的意义。又比如当我们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环境,周围的建筑、服饰、仪式都失去了熟悉的意义框架,我们会感到困惑和迷失。
神经科学的研究发现,某些脑损伤会导致患者丧失这种意义建构的能力。他们的视觉系统完好无损,能够准确地感知形状、颜色、大小,但无法将这些感知整合成有意义的对象。一个患者看到手套时,能够准确描述它是“一个连续的表面,自身折叠,有五个外突的部分”,却无法认出这是手套。这种状况揭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:我们平时理所当然的“看见”,实际上包含着复杂的意义赋予过程。
人类通过表征来理解世界。建筑之所以必然是表征性的,是因为建筑是人类创造的,而人类只能创造有意义的事物。一座没有意义的建筑是不可能被设计出来的,因为设计本身就是一个赋予意义的过程。
当建筑师构思一座建筑时,在他脑海中首先出现的不是具体的物质形态,而是关于这座建筑的“意向”——它应该传达什么感觉,应该服务什么功能,应该与环境形成什么关系。这些意向属于意义的领域,而不是物质的领域。然后,建筑师通过设计将这些意向转化为具体的形式,通过施工将形式转化为物质实体。最后,当使用者进入建筑,他们又通过感知将物质形态重新转化为意义体验。
这个循环——从意义到物质,再从物质到意义——构成了建筑存在的基本模式。在这个循环中,表征扮演着关键角色。建筑通过表征,将抽象的意向固化为可感知的形式;使用者通过解读表征,从形式中提取出意义。
因此,建筑的表征性不是建筑的一种特殊属性,而是建筑作为人造物的必然属性。正如语言必然承载意义,建筑也必然承载意义。故宫的对称轴线表征着皇权的至高无上和宇宙的秩序,天坛的圆形平面表征着天圆地方的宇宙观,现代摩天大楼的垂直线条表征着向上的雄心和技术的力量。这些表征有的显而易见,有的隐藏在形式背后,但它们共同构成了建筑的意义层次。
当你下次走过一座建筑,不妨停下来问问自己:这座建筑在对我说什么?它的形式在表征什么?通过这样的追问,你会发现建筑不再是沉默的背景,而是充满语言的存在。而这种发现,正是理解建筑的起点。